
陈能宽,湖南慈利县人,金属物理学家、爆轰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1923年5月生,1946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1947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获物理冶金博士学位。曾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和西屋电器公司研究员。1955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研究员、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实验部主任、第九研究院副院长、院科技委主任等职。1986年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1988年兼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及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中,陈能宽领导组织了核装置爆轰物理、炸药和装药物理化学、特殊材料及冶金、实验核物理等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组织并参加了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以及核装置球面同步起爆的方案制定和研究,在较短时间内攻克了技术难关,实现了预期结果。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4年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进步奖,1999年9月18日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吴明静 凌晏 逄锦桥
在长达20余年的漫长岁月里,陈能宽作为核装置全面质量的技术负责人之一,参与了我国多次核试验中大部分核装置实验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陈能宽热爱生活,懂得生活的真谛,有着为科学事业奋斗终身的澎湃激情、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永不言弃的鲜明个性。这已成为他赢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崭露头角 学成归国
1923年5月13日,陈能宽出生于湖南省慈利县江垭镇一个中产之家。湘西的奇山秀水孕育了他的灵智与情怀。1942年,陈能宽从著名的雅礼中学毕业,被保送到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大学生活给陈能宽打下了扎实的研究基础,194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但是,战乱后的中国百业凋敝,面对与理想严重脱节的现实,陈能宽积极寻求出路,次年,他考上了由政府资助的自费留学,远赴美国耶鲁大学。
在耶鲁大学,他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接着又师从哥廷根学派大师、物理冶金学的著名学者麦休森(C.H.Mathewson)教授学习,于1950年获得物理冶金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西屋电器公司任职。
在美9年,陈能宽系统钻研金属物理,做出了许多重要发现,发表了多篇有关“位错”的论文。他与R.B.Pond教授合作发表的《金属晶体中滑移线传播的微观电影显示》被公认为是金属物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创举,得到了国际冶金界同行的广泛认可。1952年10月,陈能宽在美国金属学会学术会议上宣读了这一论文后,当即引起了《纽约时报》科学记者的重视,在头版上给予新闻报道。也正是通过这篇文章,奠定了陈能宽在金属物理领域不可动摇的先驱地位。这篇文章的提出,打消了材料学界对位错理论的质疑,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1955年底,陈能宽夫妇排除美国政府的重重干扰和阻挠回国,在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工作。他以长期在多种金属单晶体形变、再结晶以及核材料在高温高压下行为方面的研究成果与经验,解决了一系列理论和实验问题,培养了一批中青年科技人才,对新中国材料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峥嵘岁月 攻克难关
1960年6月,时年37岁的陈能宽,正是思想境界、学术水平均已接近成熟的年龄,多年的学术研究进入收获季节,却突然接到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通知:调入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1964年改为院),参加我国核武器研究。
那时,我国的核武器研究近乎白手起家,中国的科学家力争靠自己的力量掌握原子弹的奥秘。陈能宽受命担任一个重要研究室的室主任,身负两项重任:设计爆轰波聚焦元件,测定特殊材料的状态方程。这两项任务都是核武器事业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
他率领一帮不满30岁的年轻人,来到官厅水库旁、长城脚下一座炸药试验场(代号17号工地),土法上马,因陋就简,在临时工号里,开始了前期炸药成型工艺试验。陈能宽身先士卒,在熊熊燃烧的火堆旁,一站十几个小时,用一口普通大铁锅和几只旧军用桶,熬煮和搅拌炸药。就这样,他们硬是用土办法浇铸出了上千枚实验炸药部件。
炸药部件还要进行打炮实验,为了抓进度,往往是上个实验部件的硝烟尚未散尽,就要打第二炮。求得数据后,研究人员就用简陋的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来分析处理。
三年饥荒时期,生活条件也很艰苦,塞外风沙弥漫,科技人员克服一切困难,患上了浮肿依然夜以继日地工作,陈能宽经常亲临一线组织实验。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过两年多几千次试验后,1962年9月,“内爆法”的关键技术环节获得验证,在化工、聚合爆轰设计、“增压”、实验测试等多方面的关键技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对核材料在高温高压下状态方程方面,解决了一系列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理论和实验问题。陈能宽和这帮年轻人果真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了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起爆元件。
两弹突破 功勋卓著
1963年,陈能宽被任命为实验部主任和“冷试验”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负责爆轰物理、高压物理、中子物理、炸药部件和核材料部件研制等任务。
他和大批科研人员响应国家号召,从长城脚下转战青海高原、塞外荒漠,为我国的核武器发展付出了难以言尽的艰辛努力。多年的科学积累和刻苦钻研,使他们很快进入了爆轰物理的前沿,并逐步开拓了中国的爆轰物理专业。陈能宽率领的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攻关队伍,在化工技术、聚合爆轰设计技术、“增压”技术、材料状态方程和相应实验测试技术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1964年2月,陈能宽被任命为二机部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这是对他的科研业绩和管理能力的充分认可,同时,也在他的肩上压上了更重的担子。当年的6月6日,进行了预定计划的全尺寸爆轰模拟试验,成功解决了核试验前一系列内爆物理学与相关的材料与工程问题,为我国首次核试验铺平了道路。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大地颤抖,天空轰鸣,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屹立天地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东方巨响,寰宇皆惊。短暂的兴奋后,陈能宽遵照上级精神,根据科技发展规律,立即率领全院职工致力于三件事:深化认识——原子弹研制的科技总结;扩大战果——原子弹要装备部队;继续攀登——向氢弹研制冲刺。
因为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的氢弹研制,既要与法国争先,又要与美、苏比速度,难度相当之大。氢弹研制过程同样也遇到了一系列必须借助实验研究来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又是多次的探索—失败—总结—再探索的过程,又是多少个不眠之夜,在陈能宽的精心指导下,仍然是他率领那支年轻科技队伍艰苦奋战,与理论设计的研究人员密切合作,将关键问题和工程科学问题逐一解决。
1967年6月17日,在祖国大西北上空出现了两个太阳——中国人自力更生研制、设计、制造的氢弹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人仅用了四年的时间,我们不但赶在法国人前面爆炸了氢弹,而且所花的时间是所有核大国中最短的。
只做不说 硕果累累
“两弹”突破后,陈能宽继续带领队伍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他不仅仅是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而且还善于带领队伍把物理成果转换成工程成果,把科学技术转换成战斗力。
陈能宽参与了中国大部分核试验的方案制定和组织领导工作。他把视线投向核试验爆炸方式的转变,将核爆炸方式从空爆、地爆逐步转向平洞和竖井试验。每次核试验,都会面临许多新的技术难题,都会使陈能宽和他的研究团队付出极大的努力和代价。每一次的成功都来之不易。
要知道,开展一次核试验耗资很大,不夸张地说,很多数据是千金难换。在核武器研制技术水平相当的情况下,我国是开展实验次数最少的国家,总共只进行了45次核试验。相比起苏联和美国上千次的试验次数,我们只是他们的零头。我国科研人员“一次实验,多方收效”,走出了一条具备中国特色的核武器科技发展道路。而陈能宽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核武器研制,既是工程规模的物理研究,也是物理深度的工程开发。如何将核试验获得的科学成果转换为手中的武器,是艰苦历程中最鲜为人知的重要部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陈能宽就和王淦昌先生共同进行了“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的探索,开展了新一代起爆方式的研究。经过十多年的不断探索与实验,陈能宽带领一大批工程师与电子学家,摸索出了一整套冷实验的物理思想、方法、技术途径以及工作制度,对我国的武器定型作出了决定性贡献。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核导弹从近程、中程一直延伸到洲际,都采用这种方法来获取定型数据,既确保了沿线居民的绝对安全,又节约了大量的国家资金。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陈能宽不再负责武器型号的爆轰物理实验,分管基础研究等工作。他从另一个层面深入思考核武器研究的深层次问题。这时的陈能宽已经深切地感受到:我国科技人员在“两弹一星”积累的科学基础上,已经建立了高技术发展的基本条件。面对世界高技术的竞争与挑战,凭借敏锐的学术感知,上世纪80年代初,陈能宽再次抓住了科技发展的脉搏,他参与了中国跟踪世界高科技发展的“863”计划的前期论证工作,并直接参加了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纲要的论证起草。
1986年7月,陈能宽被任命为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次年2月,任国家863-410主题专家组首席科学家,这一年,他已64岁。
履职新岗,陈能宽大力倡导在“两弹”研制工作中形成的技术民主,自力更生,协同创新的优良作风。在原国防科工委的领导下,他以“多做少说、多做不说”的工作作风,将全国各优势单位的科技力量集中起来协同攻关,组织专家作了大量跟踪、调研、动态分析、评估等工作,以及“863”计划有关领域的起草、制订和实施工作,为中国强激光技术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20世纪80年代,陈能宽收获了科研生涯的累累硕果。1980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2年,由他领导进行的“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获全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4年,他因多次成功领导核武器重大试验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称号。1985年,他因在“原子弹突破与武器化”和“氢弹突破与武器化”两项工作中的杰出贡献,和邓稼先一起,作为整个核武器集体的光荣代表,领取了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99年9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他和朱光亚、周光召、于敏等23位科学家一起,从江泽民总书记手中接过“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诗人情怀 坚定执着
陈能宽以擅长填词作诗扬名学界。在许多重大试验成功后,他常以诗词抒怀,认为这是科学与艺术结合的高品位精神享受。这些内涵丰富的诗句,也是核武器研制集体在极艰苦的环境下工作的真实写照。
1964年10月16日,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现场,激动不已的陈能宽赋词:东方巨响,大漠天苍朗。云似蘑菇腾地长,人伴春雷鼓掌。欢呼成果崔巍,称扬举国雄飞。纸虎而今去矣,神州日月增辉。
中子弹原理试验再获成功,他书《七绝》一首:东风报喜北山场,戈壁玉成‘合金钢’。巧夺锦囊藏浩气,天机不负苦心郎。
1992年冬,他应邀出席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召开的发展战略研讨会。会上,受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程开甲等著名科学家的推举,兴致盎然地泼墨挥毫。其中最为人传诵的句子有:许身为国最难忘,神剑化成玉帛酒,共创富强。
陈能宽喜爱古典文学,文学功底深厚。核试验前夕,指挥者和负责人总是高度紧张,有如临深渊之感。在一次核试验现场的讨论会上,他有所触动,忽然脱口背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在场的于敏先生亦感慨万千,接口背诵:“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两人一句接一句地往下背诵,在座诸人无不肃然恭听,感情随之波荡起伏。
陈能宽热爱生活,懂得生活的真谛。有着为科学事业奋斗终身的澎湃激情、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永不言弃的鲜明个性。这已成为他赢得成功的重要因素。遗憾的是,自2011年起,他卧病301医院,缓慢但持续发展的疾病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老人已经无法与人交谈。但是,在医生、亲友和同事面前,他依然表现出令人动容的坚定与执着。
2011年,在他病情还不算太严重的时候,小儿子陈子浩为他念诗,他最爱听毛主席诗词,每当听到《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时,老人就会捏紧右拳锤击自己的胸口,轻声地说:“我们,我们!”
到后来,他已不能说话应答,但是每当听到年轻时喜爱的那些慷慨激越的诗句,眼神中依旧会闪现无与伦比的神采。
2013年,他在病床上迎来了九十华诞。

①1988年,陈能宽查阅资料。

②1984年纪念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二十周年,陈能宽(右)与万里(中)、朱光亚(左)在一起参加宴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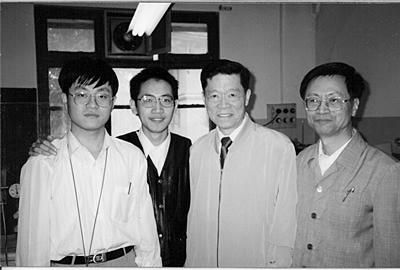
③陈能宽(右二)在实验室。
陈能宽谈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意义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五年,1964年10月16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我在现场参加试验,亲眼看到伴随着春雷般的响声和急剧升腾的蘑菇云,参试人员纵情鼓掌,热泪盈眶。我现在回想,这一举世瞩目的事件究竟给了我什么启示呢?有一段时间曾听人说,“国防科研花了那么多钱,没有搞出什么东西”。似乎中国有没有一点原子弹,关系不大,“它不能吃,不能穿,不能用,还拖了国民经济的后腿”。这些话倒促使我在回忆过去时,不能只是抒发怀旧之情,而要思考更多的问题了。
中国为什么下决心搞原子弹?
我认为最根本的理由是中国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虽然新中国政治上站起来了,但军事上还受人欺侮,经济上被人封锁,外交上不被某些大国承认,甚至有人以核讹诈威胁我们,形势是异常严峻的。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被迫下决心解决原子弹的有无问题。
值得提到的是一些老一辈科学家的献身精神和光辉榜样。他们大多是从事基础研究的,很有造诣,世界知名。如果完全从个人兴趣选择出发,研制武器的吸引力就不一定处于首位。但是,他们毅然决然以身许国,把国家安全利益视为最高价值标准。这更是国家决策深得民心的历史见证。
中国为什么能很快地搞出原子弹?
我个人体会和认识:一是目标选择对了。也就是国家的需要和实际的可能性结合得非常好。说需要,中国需要和平,但和平不能没有武器。说可能,美、苏、英、法先走了一步,证明原子弹的“可行性”已经解决。我国卓有远见的领导人同德才兼备的科技专家相结合制订的发展科学技术和研制核武器规划,加上已探明的铀矿资源、人才的准备,以及一定的工业与技术基础,都表明我们完全有可能很快搞出原子弹。
二是组织领导集中。当时各级领导都具有权威,事事有人“拍板”。中央专委以周恩来为首,更是一个具有高度权威的权力机构。全国为此事“开绿灯”,全国“一盘棋”。
三是自力更生为主。原子弹的研制技术高度保密,所以掌握技术诀窍,必须靠自力更生。我们自力更生的方式是非常生动活泼的。我们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步一个脚印,对国外走过的路力求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因而敢于攻关探险,能够少走弯路。我们注意在基础预研、单项技术和元件上下功夫,所以能够做出自己的发明创造来,而所花的人力、物力比国外却少得很多。
四是全国大力协同。毛泽东为了推动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亲笔写过一句话:“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当时,全国各个单位都以承担国防任务为荣,努力协同作战。例如,我们用的高速转镜相机和高能炸药,就是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协同完成的。诸如此类例子很多。
此外,还应提到,我们的科研组织没有“内耗”,攻关人员有献身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我们的理论、实验、设计和生产四个部门的结合是成功的,有效地体现了不同学科、不同专业和任务的结合。当时人们的献身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十分突出。他们夜以继日地奋战在草原、在山沟、在戈壁滩。即使在城市,也过着淡泊明志、为国分忧的研究生活。事实证明,为了很快地搞好尖端科研与大型经济建设,必须提倡集体主义精神。
中国搞出来原子弹究竟有什么效益?
我同意并认为:原子弹确实是一种能用但用不得、确有国家安全后效但不应多搞的“特殊商品”。这些后效可以概括为:
第一,军事上不怕核讹诈了。中国原子弹起到了遏制大国核威胁的作用,哪怕只有一颗原子弹,也不应该小看这一点东西的所谓“非线性”威慑效应所起到的自卫作用。所以,我国原子弹的研制成功对和平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第二,外交上更加独立自主了。时至今天,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转为缓和,开始以对话代替对抗,同时也进入了裁军和核禁试的征途,尖端技术走上了外交舞台。四川成都武侯祠前有一副对联,上面有一句话:“从古知兵非好战”,我从它联想到,执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中国,是不可不“知兵”的。
第三,国际地位提高了。泱泱中华不再被排挤在联合国大门之外,就是明证。中华民族也更加自信、自尊、自豪了;并且能够在安定、和平的环境中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在这“桃符万象更新”的时候,全国各族人民是不会忘记“爆竹一声除旧”的。
我感到,今天还要强调两点“后效”:一是由于早先掌握了世界前沿的尖端技术,在新的历史时期,它使国防科技在转变到为国家整个四化服务时具有优势。这里当然包括核能、核技术的和平应用。
另外,它还使中国对于70年代以来兴起的世界新技术革命,以至最近更加引人注目的高技术竞争,在若干方面有了一个较高的跟踪起点。今后国防的根本出路,应放在提高国防科学技术水平上。国防科技水平的提高同国家科学技术整体水平的提高是不可分割的。
最后一点是培养一支精干队伍,他们是宝贵的国家财富,是无名英雄。
上述“后效”联在一起,加上第一颗原子弹成功以后的第二步棋和第三步棋的成功,我相信能够充分回答某些同志的功过评说。对于国防科技工业战线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多次给予高度评价。我个人有幸和国家需要的这项工作联系在一起,虽然只是沧海一粟,但也聊以自慰。
(摘自《陈能宽自述》,见《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中国科学院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本文略有节选。)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4-08-29 第10版 印刻)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4/8/291294.shtm